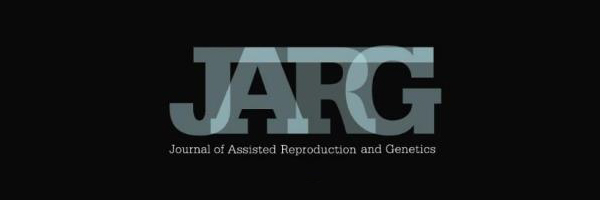“国际生殖遗传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暨湖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于长沙顺利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生殖医学与遗传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妇产科网有幸邀请到中国科学院黄荷凤院士,分享其在生殖医学与遗传学交叉研究、辅助生殖技术临床转化等尖端学科的研究经验,为广大医学同仁助力。
专家简介:

黄荷凤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殖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 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 教育部生殖遗传重点实验室主任
-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院长
- 浙江大学医学遗传与发育研究院院长
从事妇产科和生殖医学/遗传临床工作40余年,研究方向为发育源性疾病机制和遗传性出生缺陷精准防控。
记者采访:
- 以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为视角,“配子源性疾病” 理论为疾病预防等关键阶段,分别带来了哪些临床干预策略与健康管理方案?
黄荷凤院士:
- 配子源性疾病理论由本团队于2013年首次提出并在专业期刊发表,为人口健康防控体系开辟了新领域。该理论突破了传统“胎儿源性疾病”理论主要关注孕妇孕期防护的局限,将健康干预节点显著前移至孕前阶段,强调父母双方配子(精子与卵子)的健康状态对子代健康的决定性影响。例如,男性吸毒或父母肥胖均可诱导配子发生病理性表观遗传重编程,表现为DNA甲基化失衡、组蛋白修饰紊乱等广泛异常。这些表观遗传改变经受精传递至子代,不仅显著增加其出生缺陷风险,更持续影响远期健康,导致成年期代谢性疾病及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发病率升高,且此类疾病常具有隐匿性。
- 父母肥胖是典型风险因素,易导致子代高出生体重(巨大儿,>4000g),增加儿童期肥胖及成年期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之,孕前营养不良(如过度减重导致的低体重/BMI<18.5)则显著增加低出生体重儿(<2500g)风险。国际研究(如著名的荷兰饥荒研究形成的“Barker假说”)及国内研究(如贺林院士团队针对中国饥荒时期出生人群的追踪)均有力证实,低出生体重是成年期罹患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乃至精神神经障碍的独立高危因素。因此,孕前健康管理的核心策略需兼顾预防低出生体重和高出生体重。
-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胎儿出生体重的基础因素不仅在于孕期营养,更在于父母配子本身的质量。个体代谢差异(如“易胖体质”)源于基因型决定的营养物质吸收、利用效率及脂质代谢能力的不同。针对配子决定性作用的疑问,本团队2022年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母体持续高糖环境可导致卵母细胞关键去甲基化酶表达下降,使其在受精后丧失对精子基因组(特别是父源基因座)的正常去甲基化能力,引发父源基因(如葡萄糖代谢相关基因)异常高甲基化及表达失调,最终导致子代发展为1型糖尿病。重要的是,该机制并非遗传性,而是卵母细胞功能缺陷所致。通过定向修复受精卵中的表观遗传缺陷可有效逆转疾病表型,这为开发干预药物锁定了精准靶点。
- 该理论已延伸至实践。我们与华为合作研发的智能健康手环,通过持续监测体温、心率、睡眠、压力等生理指标,评估健康状态并识别不良习惯,特别集成了排卵监测功能,旨在将理论应用于全生命周期的个体化健康管理,促进健康生活方式以守护长期健康。
- 在孕妇健康研究领域,我们发现胎儿期暴露于不良环境(如母体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健康危害常迟至成年显现,增加了干预难度。若暴露胎儿为女性,其胎儿期卵母细胞受高糖环境影响导致的表观遗传改变,甚至可异常增高其未来子代(孙代)的糖尿病风险,形成跨代遗传。本团队已揭示代际遗传机制并锁定干预靶点,跨代遗传机制研究亦取得进展。这些发现凸显了孕前及孕期健康管理对阻断疾病代际传递的根本性意义。
- 为预防GDM等并发症,我们开发了整合智能手环的早期干预系统。系统结合孕妇基础信息与实时生理数据,通过预测模型评估GDM风险。对高风险者实施非药物干预,包括个体化饮食控制、运动督导(设定步数目标、提供孕期健身操视频指导及APP实时监测提醒)。对照研究证实,该方案能有效降低GDM发病率(普通人群发病率16%-20%),从而减少子代宫内高糖暴露,提升其长期健康水平。
- 鉴于慢性疾病(如高血压)难以根治的现实,防控重心需转向预防,而源头在于配子健康。基于配子源性疾病理论这一根本干预起点,我们联合华为构建了“医院-企业-公众”三位一体协作平台,深度融合医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推进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特别是在妇幼保健领域的疾病防控,成为该领域前瞻性示范模式。
黄荷凤院士专访视频: